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把SKA弄过来,弄死你我,都弄不成!”
“先弄过来!弄死你我,还有后来人!”
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家天文台工作的南仁东,最初将中国的大射电望远镜梦寄托在了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SKA上,但他发现这条路越走越难,于是开始反对在中国建SKA。南仁东的师弟彭勃却是出了名的敢想敢说敢干,师兄弟为SKA“吵”了起来。
我们到底要不要建大口径射电望远镜、在哪建、怎么建?经过多次争论、多方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在中国建设一个约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因为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也不到30米。
为了解决望远镜的支撑问题,需要找到一个天然的“大坑”,让望远镜像一口锅一样“坐”在里面;为了解决电磁波信号接收机(馈源舱)的移动问题,需要设计可靠又省钱的机械结构;为了让望远镜能够在最大范围内灵活追踪目标,需要反射面能动——这些挑战,逼出了一项项技术创新。
这个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由南仁东于1994年提出构想,历时22年建设,2016年9月25日落成启用。
“天眼”建成后,其综合性能比此前“世界最大”的阿雷西博望远镜提高了10倍,将在未来20年保持世界一流地位。以它的灵敏度,即便有人在月亮上打手机,也能够被“看见”。
“咱们中国也建一个吧!”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对老一辈天文学家来说,拥有大口径的望远镜一直是个梦。我国天文学长期落后,主要受制于望远镜设备。

二战后射电天文学方兴未艾,接连涌现类星体、脉冲星、星际分子和微波背景辐射四大天文发现,而我国在这一领域却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1993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听到这个提议后,时近50岁的南仁东兴奋不已:“如果能抓住这个时机,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就有可能领先国际几十年。”一向低调的他坐不住了,主动跑去推开中国参会代表吴盛殷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中国也建一个吧!”
南仁东最初将中国的大射电望远镜梦寄托在了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SKA身上。那是一项大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其技术路线是将上千个反射面天线和100万个低频天线组成一个超过100万平方米的接收区域,收集来自宇宙的电磁波信号。

图片来源:skatelescope.org
当时在国际射电天文圈里有两张活跃的中国面孔,一个是南仁东,另一个是他的师弟,后来成为FAST工程副经理的彭勃。他俩轮流飞往国外参加研讨,执着地想将SKA的建设引入中国。
但有天这两个互为支柱的人吵起来了。这条路越往前走南仁东越觉得走不通,他开始反对在中国建SKA。“把SKA弄过来,弄死你我,都弄不成!” 他跟彭勃说,南仁东的学术风格以“谨慎保守”著称。

“先弄过来!弄死你我,还有后来人!” 彭勃和南仁东正好相反,他外号叫“彭大将军”,出了名的敢想敢说敢干。
而后经过多次争论和多方论证,南仁东和彭勃的同门师兄,天文学家吴盛殷计算出,在中国建设一个约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最合适,既能超越已有设备,又现实可行。大家便统一想法,将SKA的梦想,嫁接到现如今的FAST身上。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个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建造计划大胆得近乎疯狂。FAST工程建设的艰难程度远超想象,它不仅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结构工程、电子学,甚至涉及岩土工程等几十个不同专业领域,且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也异常恶劣复杂。
因此,几乎所有业内专家都不看好这个项目,有人甚至认为是天方夜谭。
尽管如此,天生倔强又爱迎接挑战的南仁东决定坚持这个计划。从FAST的选址、立项、可行性研究,到指导各项关键技术的研究以及模型试验,南仁东似乎为这只“天眼”着了魔,把余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抛洒给了它。

FAST,正是“快”的意思
在国际上,用钢结构建造的望远镜,100-150米已经是工程的极限。要想做50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要依靠地势。让望远镜像一口锅一样“坐”在里面;为了解决电磁波信号接收机,即馈源舱的移动问题,需要设计一个可靠又省钱的机械结构;为了让望远镜能够在最大范围内灵活追踪天上的目标,需要望远镜反射面能动——正是这些挑战,逼出了FAST的三大技术创新。
中国西南的大山里,有着建设“天眼”极佳的地理条件:几百米的山谷被四面的山体围绕,天然挡住外面的电磁波。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坑洼众多,成了天然的候选台址。可是选择哪个作为“天眼”的家?

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没有路,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
一次,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曾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山洪裹着砂石,连人带树都能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
“有的大山里没有路,我们走的次数多了,才成了路。”“天眼”工程台址与观测基地系统总工程师朱博勤回忆,十几年下来,综合尺度规模、电磁波环境、生态环境、工程地质环境等因素,最终在391个备选洼地里选中了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的大窝凼。

立项,是最为艰难的时刻。为了推动FAST立项,南仁东每次向相关部门汇报项目都至少提前一个小时达到会场。仅仅是因为,他怕堵车迟到。那段日子,经常需要写个三五千字的项目介绍,要得很急。南仁东就和同事一起在办公室,逐字逐句斟酌,常常弄到凌晨。他怕稍有疏漏,影响项目的成败。
2007年7月,历经十几年,FAST作为“十一五”重大科学装置正式被国家批准立项。
FAST立项后,南仁东更拼命了。他一心想让“天眼”尽快建成启用。FAST,正是“快”的意思。

2010年,FAST曾经历一场近乎灾难性的风险——索网疲劳问题。当时购买的钢索进行疲劳实验后,没有一例能满足FAST的使用要求。FAST反射面的结构形式也因此迟迟定不下来。南仁东寝食难安,天天与技术人员沟通。经历近百次失败后,他终于带领团队研制出满足要求的钢索结构。

钢索的研发成功,促成了十二项自主创新专利成果的形成。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在FAST工程身上得以成功运用。
像这样创新的例子,在FAST的建造过程中不胜枚举。FAST由主动反射面、馈源支撑、测量与控制、接收机与终端、台址与观测基地等六大系统组成,每一个系统里又有很多个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里又有很多个装置。科学工作者自主设计、自主研发了FAST的绝大部分技术。

FAST馈源支撑塔开始安装时,南仁东立志第一个爬上每一座塔的塔顶。他确实这样做了。
对南仁东的这份执着,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李辉曾感到不解。现在回想起南仁东在塔顶推动大滑轮的情景,他明白了——南仁东是在用特殊的方式拥抱FAST啊!
巨大的“天眼”里,熔铸了南仁东的心血,更熔铸了他的感情。2008年底,FAST奠基时,奠基石上就刻着南仁东亲自拟的对联:“北筑鸟巢迎圣火,南修窝凼落星辰。”

发现53颗脉冲星
即将搜寻外星生命
“中国天眼”FAST——是世界上口径最大、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500米口径,其接收电波的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那么大,足足可以“装”下8个“鸟巢”体育馆。如果要给这口“大锅”装满矿泉水,能让全世界每人喝上4瓶。

FAST的大,大得有道理。只有口径越大,才能“看”得越远。科学家打过比方,以它的灵敏度,即便有人在月亮上打手机,也能被“看见”。
FAST建成后,其综合性能比此前荣膺“世界最大”的阿雷西博望远镜提高了10倍,将在未来20年保持世界一流设备的地位。有了它,不仅中国人得以透望更多天外星辰,人类的视野也得以扩展到宇宙更辽远处。
截至目前,FAST共发现了53颗脉冲星,60颗优质候选体。除了搜索脉冲星,FAST还有着更重要的科学目标,包括探测中性氢,以揭示宇宙膨胀、星系形成及演化的奥秘。以及搜寻可能存在的外星生命等等。

可以说,拥有世界领先的绝对灵敏度,让FAST拥有无限的可能。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天眼”与天宫、蛟龙、大飞机等一起,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丰硕成果。
1609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发现了月球表面高低不平的环形山,他成为利用望远镜观测天体第一人。
400多年后,代表中国科技高度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将首批观测目标锁定在直径10万光年的银河系边缘,探究恒星起源的秘密。

天文学领域的技术看上去显得“高大上”,但实际上离我们的生活却很近:射电天文学家在研究中的副产品WLAN技术,成了今天每个人生活都离不开的WIFI技术的前身;天文学类地行星的研究,让我们有了与“来自星星的你”交流的灵感……
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

如今,在喀斯特地貌的深山幽谷中,在与家人分居两地、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与世隔绝里,工作在这里的年轻人仍然像“南老师”一样,惜时如金地忙碌着——试验、调试,再试验、再调试……为的是要让FAST成为一台“好用的望远镜”。
在大山深处,在常人无法忍受的寂寞中,南仁东却用无限诗意的语言描述他们的所得:
感观安宁 万籁无声
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
召唤我们踏过平庸
进入宇宙的广袤与无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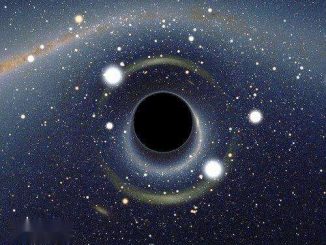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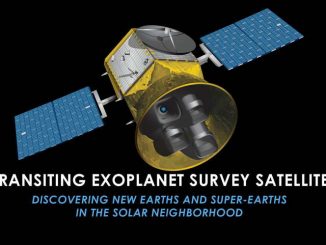
Be the first to comment